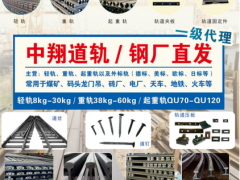最近兩三年,我國儲能產業經歷了過山車式的發展。
在2018年的高速增長之后,電化學儲能市場在2019年遭遇“寒流”,新增裝機規模下滑。而到了2020年,疫情影響之下的儲能產業逆勢增長。最新統計顯示,截至2020年6月底,中國已投運電化學儲能累計裝機規模達到1831兆瓦,同比增長53.9%。
在近日舉行的第九屆儲能國際峰會上,中國能源研究會儲能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海生表示:“我們對中國儲能已進入‘春天’的判斷沒有變,但距離行業繁榮的‘夏天’,還需要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。”
何時能進入夏天,取決于一個問題:誰來為儲能買單。
春天已至
儲能的價值何在?答案有很多。
我國的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,調控手段捉襟見肘,成為我國電力系統運行的最大風險。而儲能裝置可實現負荷削峰填谷,增加電網調峰能力;也可參與調頻調壓,提高電網安全穩定性。
2018年的市場爆發正是受到電網側項目建設的拉動。以國家電網為首的大型能源企業在江蘇、河南等地投運了百兆瓦級的儲能項目,以保障電網安全運行。
“我們預測到2025年電力系統調節能力的缺口仍有8000萬~1億千瓦左右,而且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富集的三北地區。”國家電力調度控制中心黨委書記董昱說。
2005年我國頒布《可再生能源法》之后,我國新能源發展步入快車道。截至今年7月底,國網新能源裝機累計達3.65億千瓦時,裝機占比22.9%,成為國家電網第二大電源。
董昱表示,新能源超常規發展給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帶來巨大挑戰,這也正是儲能的發展機遇。
但是,在新能源大發展的十年間,儲能的發展卻沒有跟上步伐。2016年時,國家電網區域內新能源棄電量達到465億千瓦時,并多次發生大規模集中脫網事件。
到了今年,國家發改委、能源局、科技部以及10余個省份和地區出臺相關政策,要求新能源裝機配置儲能。陽光電源副總裁吳家貌透露,可再生能源+儲能并網占比從2019年的17%增加至今年的43%,正在成為行業標配。
據國網能源研究院預測,我國新能源裝機規模到2035年將超越火電成為主力電源,達到9億千瓦。如果按平均10%的容量配置儲能,可帶來億千瓦級的儲能市場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立泉亦表示:“能源形勢逼人,挑戰逼人,使命逼人,一定要大力發展儲能,構建能源互聯網,保證能源安全。”
誰來買單
雖然政產學研用各方對儲能的前景都持積極態度,但缺乏商業模式、無人為儲能買單,卻是困擾行業發展多年的“心病”。
“可能有點‘老生常談’,但確實一直沒有解決。”在第九屆儲能國際峰會上發言時,吳家貌一開口便道出了心中的無奈,“國家出臺的政策非常好,但儲能在市場上一直是個畸形兒。”
他指出,從發電側來說,誰為新能源儲能付費并不確定;從電網側來說,沒有理清計價機制,政策也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;用戶側則收益單一,沒有體現出儲能真正的價值。此外,儲能還面臨著非技術成本較高、標準缺失、系統集成設計能力參差不齊三大挑戰,阻礙行業安全、健康發展。
寧德時代副總裁譚立斌則表示,就算成本再降低,對一些應用場景來說還是額外付出,因此,經濟模型和商業模式是國內市場的最大問題。“市場成長需要頂層設計。”他說。
2019年以來,多個百兆瓦和吉瓦級儲能項目啟動或者落地。其中就包括總裝機規模1250兆瓦的山東肥城壓縮空氣儲能調峰電站項目,這也是全球首個吉瓦級壓縮空氣儲能項目。
對于項目前景,作為技術提供方,陳海生表示:“最重要的還是商業模式。”
陳海生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,儲能必須打破目前依附于發電、電網或用戶的狀態,以獨立儲能電站的身份進入市場,才能得到合理的多方收益,真正繁榮發展。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機制,便無法真正體現出儲能的價值,也就無法激發資本的信心和市場的活力。
“明確‘誰受益、誰承擔’的原則,建立發電、電網、用戶共同承擔的合理的儲能價格機制是當務之急。”陳海生說。
送春迎夏
對于探索商業模式的呼聲,能源主管部門并非沒有回應。
近年來,國家能源局聯合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共同印發了相關政策文件,落實了支持儲能發展的具體措施。今年7月,國家能源局啟動首批儲能試點示范項目申報。國家能源局監管總監李冶表示,希望通過示范項目促進儲能規模化、標準化、市場化和產業化發展,培育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商業模式。
“國家能源局一直高度重視儲能工作,并且和行業共同配合、積極探索。”李冶說。
青海省共享儲能項目則是被業界寄予厚望的一次探索。該項目依托新能源大數據平臺,建立儲能與電網互動的數據共享網絡,通過電量交易緩解清潔能源高峰時段電力電量消納困難。今年5月9日到8月16日,通過青海共享儲能服務市場,整個青海三江源地區實現了連續100天完全使用綠色能源。
陳海生表示,儲能產業目前已探索出了一些可行的商業模式,如共享儲能、容量租賃、輔助服務等,使得儲能單位造價下降、使用頻率增加,盡管仍在夾縫中求生存,但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。
據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統計,截至2020年6月底,中國已投運儲能項目累計裝機規模為32.7吉瓦,占全球的17.6%,同比增長4.1%,實現穩中有升。
“儲能作為一個新興行業,發展一定會有波動,但隨著可再生能源占比越來越高,電力系統對于儲能長期、持續的需求是大勢所趨。”陳海生預計,“十四五”期間,儲能行業將逐步實現從商業化初期向規模化發展的轉變,到“十四五”末期或者稍晚一點的時間,光伏+儲能或可在平價水平上具有競爭力,迎來行業繁榮發展的“夏天”,并成為我國戰略性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之一。
“儲能的價值是沒有人認識到嗎?我認為不是,而是大家都認為跟自己無關。”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夏清直言,建立可體現儲能價值的輸配電市場,儲能就能迎夏送春。 中國科學報 作者: 陳歡歡
在2018年的高速增長之后,電化學儲能市場在2019年遭遇“寒流”,新增裝機規模下滑。而到了2020年,疫情影響之下的儲能產業逆勢增長。最新統計顯示,截至2020年6月底,中國已投運電化學儲能累計裝機規模達到1831兆瓦,同比增長53.9%。
在近日舉行的第九屆儲能國際峰會上,中國能源研究會儲能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海生表示:“我們對中國儲能已進入‘春天’的判斷沒有變,但距離行業繁榮的‘夏天’,還需要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。”
何時能進入夏天,取決于一個問題:誰來為儲能買單。
春天已至
儲能的價值何在?答案有很多。
我國的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,調控手段捉襟見肘,成為我國電力系統運行的最大風險。而儲能裝置可實現負荷削峰填谷,增加電網調峰能力;也可參與調頻調壓,提高電網安全穩定性。
2018年的市場爆發正是受到電網側項目建設的拉動。以國家電網為首的大型能源企業在江蘇、河南等地投運了百兆瓦級的儲能項目,以保障電網安全運行。
“我們預測到2025年電力系統調節能力的缺口仍有8000萬~1億千瓦左右,而且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富集的三北地區。”國家電力調度控制中心黨委書記董昱說。
2005年我國頒布《可再生能源法》之后,我國新能源發展步入快車道。截至今年7月底,國網新能源裝機累計達3.65億千瓦時,裝機占比22.9%,成為國家電網第二大電源。
董昱表示,新能源超常規發展給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帶來巨大挑戰,這也正是儲能的發展機遇。
但是,在新能源大發展的十年間,儲能的發展卻沒有跟上步伐。2016年時,國家電網區域內新能源棄電量達到465億千瓦時,并多次發生大規模集中脫網事件。
到了今年,國家發改委、能源局、科技部以及10余個省份和地區出臺相關政策,要求新能源裝機配置儲能。陽光電源副總裁吳家貌透露,可再生能源+儲能并網占比從2019年的17%增加至今年的43%,正在成為行業標配。
據國網能源研究院預測,我國新能源裝機規模到2035年將超越火電成為主力電源,達到9億千瓦。如果按平均10%的容量配置儲能,可帶來億千瓦級的儲能市場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立泉亦表示:“能源形勢逼人,挑戰逼人,使命逼人,一定要大力發展儲能,構建能源互聯網,保證能源安全。”
誰來買單
雖然政產學研用各方對儲能的前景都持積極態度,但缺乏商業模式、無人為儲能買單,卻是困擾行業發展多年的“心病”。
“可能有點‘老生常談’,但確實一直沒有解決。”在第九屆儲能國際峰會上發言時,吳家貌一開口便道出了心中的無奈,“國家出臺的政策非常好,但儲能在市場上一直是個畸形兒。”
他指出,從發電側來說,誰為新能源儲能付費并不確定;從電網側來說,沒有理清計價機制,政策也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;用戶側則收益單一,沒有體現出儲能真正的價值。此外,儲能還面臨著非技術成本較高、標準缺失、系統集成設計能力參差不齊三大挑戰,阻礙行業安全、健康發展。
寧德時代副總裁譚立斌則表示,就算成本再降低,對一些應用場景來說還是額外付出,因此,經濟模型和商業模式是國內市場的最大問題。“市場成長需要頂層設計。”他說。
2019年以來,多個百兆瓦和吉瓦級儲能項目啟動或者落地。其中就包括總裝機規模1250兆瓦的山東肥城壓縮空氣儲能調峰電站項目,這也是全球首個吉瓦級壓縮空氣儲能項目。
對于項目前景,作為技術提供方,陳海生表示:“最重要的還是商業模式。”
陳海生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,儲能必須打破目前依附于發電、電網或用戶的狀態,以獨立儲能電站的身份進入市場,才能得到合理的多方收益,真正繁榮發展。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機制,便無法真正體現出儲能的價值,也就無法激發資本的信心和市場的活力。
“明確‘誰受益、誰承擔’的原則,建立發電、電網、用戶共同承擔的合理的儲能價格機制是當務之急。”陳海生說。
送春迎夏
對于探索商業模式的呼聲,能源主管部門并非沒有回應。
近年來,國家能源局聯合國家發改委等有關部門共同印發了相關政策文件,落實了支持儲能發展的具體措施。今年7月,國家能源局啟動首批儲能試點示范項目申報。國家能源局監管總監李冶表示,希望通過示范項目促進儲能規模化、標準化、市場化和產業化發展,培育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商業模式。
“國家能源局一直高度重視儲能工作,并且和行業共同配合、積極探索。”李冶說。
青海省共享儲能項目則是被業界寄予厚望的一次探索。該項目依托新能源大數據平臺,建立儲能與電網互動的數據共享網絡,通過電量交易緩解清潔能源高峰時段電力電量消納困難。今年5月9日到8月16日,通過青海共享儲能服務市場,整個青海三江源地區實現了連續100天完全使用綠色能源。
陳海生表示,儲能產業目前已探索出了一些可行的商業模式,如共享儲能、容量租賃、輔助服務等,使得儲能單位造價下降、使用頻率增加,盡管仍在夾縫中求生存,但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。
據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統計,截至2020年6月底,中國已投運儲能項目累計裝機規模為32.7吉瓦,占全球的17.6%,同比增長4.1%,實現穩中有升。
“儲能作為一個新興行業,發展一定會有波動,但隨著可再生能源占比越來越高,電力系統對于儲能長期、持續的需求是大勢所趨。”陳海生預計,“十四五”期間,儲能行業將逐步實現從商業化初期向規模化發展的轉變,到“十四五”末期或者稍晚一點的時間,光伏+儲能或可在平價水平上具有競爭力,迎來行業繁榮發展的“夏天”,并成為我國戰略性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之一。
“儲能的價值是沒有人認識到嗎?我認為不是,而是大家都認為跟自己無關。”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夏清直言,建立可體現儲能價值的輸配電市場,儲能就能迎夏送春。 中國科學報 作者: 陳歡歡
 手機版|
手機版|

 關注公眾號|
關注公眾號|


 下載手機APP
下載手機APP